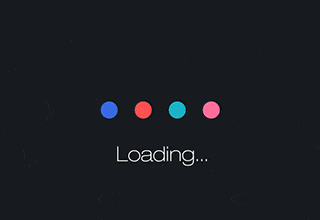废都碎瓦
庄之蝶让唐宛儿坐下,说道﹕「你是有福的,就你这长相,也不是薄命人。过去的事过去了。现在不是很好吗﹖」
唐宛儿说﹕「这算什么日子﹖西京虽好,可哪里是我长居的地方﹖庄老师你还会看相,就再给我看看。」
妇人将一只白生生的小手伸过来,放在庄之蝶的膝盖上了。
庄之蝶握过手来,心里是异样的感觉,胡乱说过一气,就讲相书上关于女人贵贱的特徵,如何额平圆者贵凹凸者贱,鼻耸直者贵陷者贱,发光润者贵枯涩者贱,脚跗高者负扁薄者贱。
妇人听了,一一对照,洋洋自得起来。只是不明白脚怎么个算是跗高,庄之蝶动手去按她的脚踩下的方位,手要按到了,却停住,空里指了一下,妇人却脱了鞋,将脚竟能扳上来,几乎要挨着那脸了。
庄之蝶谅讶她腿功这么柔韧,看那脚时,见小巧玲珑,脚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大脚趾老长,后边依次短下来,小脚趾还一张一合地动。
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
看着妇人重新穿好袜子和鞋,间﹕「你穿多大的鞋﹖」
妇人说﹕「三十五号码的。我这么大的个,脚太小,有些失比例了。」
庄之蝶一个闪笑,站起来说﹕「这就活该是你的鞋了﹗」
从兜里取了那双皮鞋给妇人。
唐宛儿说﹕「这么漂亮的!多少钱﹖」
庄之蝶说﹕「你要付钱吗﹖算了,送了你了﹗」
妇人看着庄之蝶,庄之蝶说﹕「穿上吧﹗」
庄之蝶又说﹕「有个叫唐图的,是你什么人﹖」
唐宛儿说﹕「是我弟弟,他喜欢夸夸其谈,那件事知道的,我弟弟人不太实在,老以为和一些稍微有知名度的人争争拗拗就有满足感,都不怕骚扰人家的正常工作﹗喂﹗别跟他一般见识啦﹗今天你准备把我怎样﹖」
「这里不方便,跟我来。」庄之蝶说完便出门。
唐宛儿随后到了七零三房间,庄之蝶一下子关了门,就把妇人抱起来。
妇人乖觉,任他抱了,且双腿交合在他腰际,双手攀了他脖颈,竟如安坐在庄之蝶的双手上。
妇人说﹕「瞧你刚才那个小心样子,现在就这么疯了﹖」
庄之蝶只是嘿嘿笑,说﹕「我好不想你,昨儿晚上还梦到了你,你猜怎么着,我背你上山,背了一夜。」
妇人说﹕「那真不怕累死了你﹗」
庄之蝶就把妇人放在床上,揉着如揉一团软面。
妇女笑得咯儿咯儿喘,突然说﹕「不敢动的,一动下边都流水儿了。」
庄之蝶一时性起,一边咽着泛上来的口水,一边要剥妇人的衣裙。
妇人站起却自己把衣裙脱了,说走路出了汗,味儿不好,她要冲个澡的。
庄之蝶就去里间浴池里放水,让她去洗,自个平静下心在床边也脱了衣服等待。
一等等不来,几自推了浴室门,见妇人一头长发披散,一条白生生身子立于浴盆,一手拿了喷头,一手揣那丰乳,便扑过去。
妇人顿时酥软,丢了喷头,坐进浴盆里,庄之蝶拿块凳坐在旁边,上下其手,一时捏弄奶子,一时挖弄牝户,一时又去吻她的嘴脸,忙个不乐亦乎。
妇人的头枕在盆沿,长发一直撒在地上,任庄之蝶在仰直的脖子上咬下四个红牙印儿,方说﹕「别让头发沾了水。」
庄之蝶才爬起来,关了喷头,将她平平的端出来放在床上。
床头是一面小桌,桌上面的墙上嵌有一面巨镜,妇人就在镜里看了一会,笑着说﹕
「你瞧瞧你自己,哪儿像个作家。
庄之蝶说﹕「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儿﹖」
妇人说﹕「应该文文雅雅吧﹗人家对稿的,都懂得大谈『合理性』,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你这个作家大作家就那么没廉耻﹗」
庄之蝶说﹕「哈哈﹗那小子闭着眼睛说瞎话,我现在就来将你欺﹗」
说着就把妇人双腿举起,去看那一处穴位,羞得妇人忙说﹕「不,不的。」
却再无力说话,早有一股东西涌出,随后就拉了被子垫在头下,只在镜里看着。
庄之蝶已箭在弦上,扑上身去,就一阵没头没脑的狂插急抽去来。
直到妇人口里喊叫起来,庄之蝶忙上来用舌头堵住,两人都只有吭吭喘气。
妇人说﹕「要命的,你夺了我的魂了﹗」
庄之蝶说﹕「还没出来哩﹗要不要做预防措施﹖」
妇人说﹕「你射进去吧﹗我是有备而来的﹗」
庄之蝶又是一阵急动,才贴紧妇人的下盘,两扇屁股急剧抽搐。
完事后,妇人亮着裸体坐起,望着淫液浪汁横溢的牝户说道﹕「你出得好多﹗」
庄之蝶说﹕「有没有见到你阴唇上有一颗痣﹖」
妇人听说她那里竟有一颗痣的,对着镜寻着看了,心想庄之蝶太是爱她。潼关的那个工人没有发现,老公也没有发现,连她自己也没发现,就说﹕「有痣好不好﹖」
庄之蝶说﹕「可能好吧,我这里也有痣的。」
看时,果然也有一颗。
妇人说﹕「这就好了,以后走到天尽头,我们谁也找得着谁了﹗」
说毕,却问﹕「门关好了没,中午不会有人来吧﹖」
庄之蝶说﹕「你现在才记起门来了,我一个人的房间,没人的。」
次日,唐宛儿又来找庄之蝶。
关门之后,妇人就让庄之蝶抱她在怀,说﹕「咱一来就干这事,热劲倒比年轻时还热﹗」
庄之蝶抬头看她的时候,她就吟吟地给他笑,想要说些什么,却不知说些什么,后来就说﹕
「今天一个乡里人到北大街,四处找不到厕所,瞧见一个没人的墙根,就极快地拉了大便,刚提裤子,警察就过来了,他忙将头上的草帽取下来把大便盖了,并拿手住。警察问﹕‘干什么﹖’乡里人说﹕‘逮雀儿。’警察就要揭草帽。乡里人说﹕『不敢揭的,待我去那家店里头拿个鸟笼来﹗』,就逃之夭夭,而警察却一直那么小心地按着草帽。有意思吧﹖」
庄之蝶笑了一下,说﹕「有意思。可我们要干好事,你却说大便。」
唐宛儿就叫道﹕「哎哟,你瞧我﹗」
倒拿拳头自己打自己头,然后笑着去厨房拿手巾。
她那修长的双腿,登了高跟鞋,走一字儿步伐。手巾取来了,庄之蝶一边擦着嘴一边说﹕「宛儿,平日倒没注意,你走路姿势这么美的﹗」
妇人说﹕「你看出来啦﹖我这左脚原有一点外撇,我最近有意在修正,走一字儿步伐。
庄之蝶说「你再走着让我看看。」
妇人转过身去,走了几下,却回头一个媚笑、拉开厕所门进去了。
庄之蝶听着那哗哗的撒尿声,如石涧春水,就走过去,一把把门儿拉开了,妇人白花花的臀部正坐在便桶上。
妇人说﹕「你出去,这里味儿不好。」庄之蝶偏不走,突然间把她从便桶上就那么坐着的姿势抱出来了。
妇人说﹕「今日不行的,有那个了。」
果然裤头里夹着卫生巾。庄之蝶却说﹕「我不,我要你的,宛儿,我需要你﹗」
妇人也便顺从他了。
他们在床上舖上了厚厚的纸,唐宛儿仰卧下去,两条白玉的嫩腿举高起来,庄之蝶提枪对那裂缝插了进去,血水喷溅出来,如一个扇形印在纸上,有一股儿顺了瓷白的腿面鲜红地往下蠕动动,就一条虹蛔虫。
妇人说﹕「你只要高兴,我给你流水儿,给你流血。」
庄之蝶避开她的目光,把妇人的头窝在怀里,说﹕「宛儿,我现在是坏了,我真的是坏了﹗」
妇人钻出脑袋来,吃惊地看着他,闻见了一股浓浓的烟味和酒气,看见了他下巴上一根剃须刀没有剃掉的胡须,伸手拔下来,说﹕「你在想起她了吗﹖你把我当她吗﹖」
庄之蝶没有作声,急促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妇人是感觉到了。
但庄之蝶想到的不仅是他妻子牛月清,也想到另一个女人景雪荫。
这瞬间里他无法说情为什么就想到她们,为什么要对唐宛儿这样﹖
经她这么说了,他竟更是发疯般地将她翻过身来,让双手撑在床上,不看她的脸,不看她的眼晴,楞头闷脑地从后边去,两手捏着唐宛儿双乳,那血淋淋的东西塞入还在淌血的洞儿噗哧噗哧的抽插。血水就吧嗒吧嗒滴在下面的纸上,如一片梅瓣。
也不知道了这是在怨恨着身下的这个女人,还是在痛恨自己和另外的两个女人,直到精洩,倒在了那里。
倒在那里了,深沉低缓的哀乐还在继续地流泻。
两人消耗了精力,就都没有爬起来,像水泡过的土坯一样,就都稀软得爬不起来,谁也不多说一句话,躺着闭上眼睛。唐宛儿不觉竟磕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来,庄之蝶还仰面躺着,却抽烟哩。
目光往下看去,他那一根东西却没有了,忽地坐起来,说﹕「你那…」
庄之蝶平静地说﹕「我把它割了。」
唐宛儿吓了一跳,分开那腿来看,原是庄之蝶把东西向后夹去,就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吓死我了﹗你好坏﹗」
临走,唐宛儿说﹕「我带给你一只鸽子,在你们这儿养几天,也让它认认你们,这些日子你放开,它能认得我这儿的。」
庄之蝶想﹕买鸽子当电话使呀,她竟也这么想的呢﹗就喜欢地说﹕「好的。」
抱了鸽子,拿回家让保母柳月养着。
柳月养了鸽子,每日庄之蝶都要买些谷子来餵,几天后,在鸽子脚环上别了一封短信,约唐宛儿到他家。
那妇人看了条儿,遂又写了条子让鸽子先回去,自已就在家着意收拾打扮起来。
活该要事情暴露,等鸽子再飞来时,柳月偏巧在凉台上晾衣服,觉得奇怪﹕鸽子才放回去的,怎么又飞来了﹖就看见鸽脚环上有个小小纸条,抱住取了一看,上面写道﹕
「我早想去你家的,在你家里玩着我会有女主人的感觉。」
认得是唐宛儿的笔迹,心里就想﹕早看出他们关系超出一般,没想已好到这个价儿上,不知以前他们已捣鼓了多少回,只瞒得夫人不知道,我也眼晴瞎了﹗就不做声把纸条重新放好,悄声回到厨房,对庄之蝶喊﹕「庄老师,鸽子在那儿叫哩﹗」
庄之蝶过去抱了鸽子,又在凉台上放下了,走来厨房说﹕「哪里有鸽子,鸽子不是放飞走了吗﹖柳月呀,今日你大姐去双仁府那边了,她干表姐一家来看老太太的,那里人多,你大姐做饭忙不过来,你也过去帮她吧。我这里你不用管了。」
柳月在心里说﹕你这话以前对我说,我都怕你骗信了,今日还要想骗我吗﹖口里就应道﹕「那好嘛﹗」
柳月其实没有走远,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心里乱糟糟的不是味道。估摸唐宛儿已经去了家,就走回来,也不叫门,到了隔壁人家,推说出门忘了带钥匙,要藉人家的凉台翻过去开门。
这楼房的凉台是连接的,中间只隔一个水泥挡墙,以前几次忘带钥匙,就是这么翻凉台进的屋。
当下蹑脚蹑手过来,悄声潜入自己睡的房间,又光了脚,贴墙走到庄之蝶的卧室门口,那卧室门没有关,留有一个缝儿。
还未近去。就听见里边低声浪笑。
庄之蝶说﹕「把衣服穿上吧,那柳月丢三拉四的,说不定半路就又折回来拿什么东西﹗」
柳月就在心里发恨﹕你讨好人家,倒嚼我的舌根子,我什么时候丢三拉四了﹖便听唐宛儿说﹕「我不嘛。我还要的。」
柳月估摸,他们是干过了,不知庄之蝶拿了夫人什么好东西送她,她竟还嫌不够﹗
伸头从门缝往里看时,竟是唐宛儿赤条条睡在床沿,双手抓了庄之蝶的东西,又捋又套的,媚眼中淫光四射。
庄之蝶就说﹕「我不来了,你总说我求你的,我今日要你得求着我。」
唐宛儿说﹕「我也不求你的,只让你给我再摸摸就行。」
庄之蝶就头俯下去,一边在那奶子上吸吮,一手在唐宛儿下边去,唐宛儿也滚动起来,要他上去,他笑着偏不。
就口里一声儿乱叫不已,说,"我求你了,是我求你了,你让我流多少水儿出来才肯呢﹖」
柳月看见那腿中间已水亮亮一片,一时自己眼花心慌,一股东西也憋得难受,唿地流了下来,要走开,又迈不开脚,眼里还在看着,庄之蝶就上去了,眼见那一条长长的硬棒直插水光湿现的洞眼。
唐宛儿一声惊叫,头就在那里摇着,双手痉挛一般抓着床单,床单便抓成一团。
柳月也感觉自己喝醉了酒,身子软倒下来,把门撞开了。
这边一响动,那边妻时间都惊住了。
待看清是柳月,庄之蝶忙抓了单子盖了唐宛儿,也盖了自己,只是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就进来了﹖﹗」
柳月翻起来就往出跑。
庄之蝶叫着「柳月,柳月。」就急得寻裤子,偏是寻不着,口里说﹕「这下坏了,她是要给月清说的。」
唐宛儿却把他拿着的一件衫子夺下,说﹕「她哪里就能说了﹖」
竟把赤裸裸的庄之蝶往出推,一边推,一边努嘴儿。
庄之蝶就撵出来,见柳月已靠在她房间的床背上,唿哧砾唿哧喘气。
庄之蝶说﹕「柳月,你要说出去吗﹖」
柳月说﹕「我不说的。」
庄之蝶一下子抱住她,使劲地去剥她的衣服。
柳月先是不让,但剥下衫子了,就不动弹了,任着把裤子褪开,庄之蝶看见她那裤子里也是湿漉漉了一片,说﹕「我只说柳月不懂的,柳月却也是熟透了的柿蛋﹗」
两人就压在床沿上,庄之蝶把那沾满唐宛儿淫液浪汁的肉棒对着柳月双腿间的凹处硬生生逼入,插了两插,心里一动,不禁抽出一望。
庄之蝶说﹕「柳月,你怎地不见红,你不是处女,和哪个有过了﹖」
柳月说﹕「我没有,我没有﹗」
身子已无法控制,扭动如蛇。
唐宛儿始终在门口看着,见两人终于分开,过去抱了柳月说﹕「柳月,咱们现在是亲亲的姐妹了。」
柳用说﹕「我哪能敢给你作亲姐妹,今日我若不撞着,谁会理我的﹖他理了我,还不是要封了找的口﹗」
心里倒觉得后悔万分,以前庄之蝶对她好感过,她还那么故意清高,寻思着要真正赢得他的,没想如今却这般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想着就眼泪流下来。庄之蝶说﹕「柳月是稀人才,我哪里没爱着,又哪日不是在护了你﹖可你平日好厉害的,我真怕你是你大姐叮嘱了要监视我的。」
柳月说﹕「大姐肯信了我﹖她也常常防了我的。你们闹矛盾,她气没处出,哪日又不是把我当撤气筒﹗」
庄之蝶说﹕「你不要管她,以后有什么过失的事儿,你就全推在我身上﹗」
柳月就更伤心,嘎嘎哭起来。
庄之蝶和唐宛儿见她一时哭得劝不住,就过来穿衣服。
唐宛儿说﹕「今日这事好晦气的,偏让她撞见了。」庄之蝶说﹕「这也好,往后也不必提心吊胆的。」
唐宛儿说﹕「我知道你心思,又爱上更年轻的﹗我刚才是看着你的,要封她的口也用不着和她那个,你是主人家,吓唬一下,她哪里就敢胡言乱语﹖你偏真枪真刀地来,就是要干那个,你应付一下也就罢了,竟是那么个热腾劲儿﹖她是比我鲜嫩。你怕以后就不需要我了﹗」
庄之蝶说﹕「你瞧你这女人,成也是你,不成也是你﹗」
唐宛儿便说﹕「我提醒你,她是个灾星的。你们干着,我看着了,她是没长毛的。人常说没毛的女人是白虎煞星,男人有一道毛从前胸直到后背了这叫青龙,青龙遇白虎是带福,若不是青龙却要退了百虎就会带灾。今日你与她干上了,说不定就有灾祸出来的,你得好自为之。」
直说得庄之蝶也心惊然起来,送她走了,自个冲了一怀红糖开水到书房去喝了。
庄之蝶却并未听从唐宛儿的话,与柳月有了第一次,也便有了二次三次,还特意察看,这尤物果真是白虎,但丰隆鲜美,开之艷若桃花,闭之自壁无暇,也就不顾了带灾惹祸的事情。
一日,庄之蝶写了个把钟头,写得烦躁,觉得口渴,来厨房找什么吃,见案上一盘梅李,拿一颗吃了,让柳月也来吃。
喊了一声,柳月没应,过来卧室见柳月仰面在床上睡着了。
柳月解开的褂子上,一只钉好的扣子线并没有断,线头还连着针,乳罩下的一片肚皮细腻嫩白。
庄之蝶笑了一下,却忍禁不住,轻轻解了乳罩,也把那裙带解开,静静地欣赏一具玉体。
只见柳月那白雪雪的肉桃儿忒煞爱死人了﹗
庄之蝶伯弄醒了她,便拿了梅李在上边轻摩,没想那缝儿竟张开来,半噙了梅李,庄之蝶无声地笑笑赶忙悄然退出,又去书房里写那答辩。
写着写着,不觉把这事就忘了。
约摸十点左右,柳月醒来,才发觉衣服末扣,乳罩和裙子也掉下来,同时下边憋得张胀地痛,低头一看,噢地就叫起来。
庄之蝶勐地才记起刚才的事,忙关了门走过来,柳月偏也不取了梅李,说﹕「老师就是坏﹗」
庄之蝶佯装不知,说﹕「老师怎么啦﹖」
接着说﹕「哟,柳月,你那儿怎么啦,是咸泡梅李罐头吗﹖」
柳月说﹕「就是的,糖水泡梅李,你吃不﹖」
庄之蝶竟过去,把她压住,要取了梅李,梅李却陷了进去。瓣开取了出来,就要放进口去咬。
柳月说﹕「不干净的。」
庄之蝶说﹕「柳月身上没有不干净的地方。」
径自咬了一口,柳月就把那一半夺过也吃了,两人嘻嘻地笑。
柳月却说﹕「你在戏弄我哩,做这恶作剧,是唐宛儿你敢吗﹖」
庄之蝶说﹕「我让你吃梅李,你睡着了,样子很可爱,就逗你乐乐﹗」
柳月说﹕「你哪里还爱我﹖我在你心里还不是个保姆﹖」
庄之蝶再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说过了那番话后还在激动的柳月,他轻声唤道﹕
「柳月﹗」
柳月就扑过来,搂抱了他,他也搂抱她。
柳月一股泪水流下来,咯咯地滴在庄之蝶的手臂上,说﹕「庄老师,能让我像唐宛儿一样吗﹖」
她说着,眼睛就闭上了,一只手把睡袍的带子拉脱,睡袍分开了,像一颗大的话的荔枝剥开了红的壳皮,里边是一堆玉一般的果肉。
庄之蝶默默地看着,把桌上的台灯移过来拿在手里照着看,只见灯下的人儿更加迷惑,不禁放下灯,把柳月的肉身放在沙发,抽起脚踝,分开双腿,狠命弄干起来。
柳月叫了一声,那沙发就一下一下往门口推动,最后顶住了房门,咯地一声,把两人都闪了一下,柳月的头窝在那里。
庄之蝶要停下来扶正她,她说﹕「我不要停的,我不要停的﹗」
双腿竟蹬了房门,房门就发出眶眶的响动,身子撞落了挂在墙上的一张条幅,哗哗啦啦掉下来盖住他们。
柳月说﹕「字画烂了。」
庄之蝶也说﹕「字画烂了。」但他们并没有了手可去取字画。